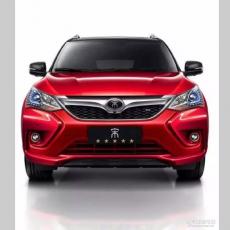萨 菈
我正走在中关村熙熙攘攘的街头,忽然接到东北友人的电话:七军的王铁环走了。
那天正值“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夜,最后的抗联女战士又少了一位。当我回过神来,一对父女手牵着手正从身边走过,那个女孩粉雕玉琢,仿佛是从年画上走下来的人物。
忽然一惊,一瞬间,王铁环老人的形象竟和这个一蹦一跳的女孩子重合在了一起。
而王铁环的童年,却没有眼前女孩的这种幸福。她八岁时,跟着父亲上山打鬼子,在山道上奔走如飞做交通员。抗联的老兵们都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日军归屯并户和疯狂的扫荡下,抗联的补给日益艰难。后勤部队的女兵们努力为大家改善生活,七军的驻地周围有很多星罗棋布的泡子,即小湖,大家行军之余便设法去钓鱼。王铁环当时只有十二岁,生得瘦小,于是她把鱼线拴在了自己的脚腕儿上。等了许久都没有鱼上钩,她渐渐有些困倦。睡眼迷离间,忽然觉得脚被什么东西拽着往湖里拖。
或许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的水边,东北有溺死鬼找人替代的传说,会把经过河边的人拖下水,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样的故事。
当时王铁环肯定吓坏了,她一面拼命撑持着不被拖走,一面大声喊叫。
叫声惊动了附近的抗联官兵,大家赶来营救,才发现原来王铁环拴的渔线在往水里拽她。大家一起动手,结果拉上来一条一米多长的巨型鲶鱼。
部队打了牙祭,有的战士对这个会钓大鱼的小姑娘开玩笑糗她一下:“好家伙,好悬没把我们铁环当鱼食啊!”
因为这个故事,王铁环在我心目中,便是年画上那个抱着大鱼的小姑娘。
就像小兵张嘎永远定格在那个充满个性的嘎小子身上一样,谈起王铁环,总没想到老人家已届耄耋。因为我们采访的抗联老兵几乎都比她大,说起她的故事,都带着一种对小妹妹的宠爱。当噩耗真正传来时,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抗联最年轻的女兵也已经早过米寿。
在抗联的编制中,每个军也许有好几个师,也许只有一个师,但有两个编制是少不了的,一个是担负军部安全和政治保卫任务的警卫旅,一个便是少年连。
少年连的战士,几乎都是孤儿或烈士遗属,他们年纪虽小,但都英勇坚定,视死如归。在一次次和日军的血战中,这些中国少年无畏的身影让敌人惊叹。
而每一位首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这些尚未长成的孩子。
王铁环是这些少年抗联战士中的一个缩影,十来岁的她已经在战火纷飞的沙场上充当通信员,刚刚长得比枪高一点,便朝敌人开了枪。当杨靖宇和赵尚志两位抗联总司令战死沙场时,这个刚刚青春的生命,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不仅是王铁环,在最艰苦的时刻,很多少年抗联战士和女兵都活下来了。几十年后,人们才理解他们得以活下来的原因。
二○一○年,在日本发现的《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战史》中,记录了抗联政委魏拯民在最后时刻写下的信件。在敌众我寡、战斗已至最后关头的关键时刻,这位有着一副书生面孔的中国抗联将领用信件发出了一道或将永远被人铭记的命令:老人、伤员和女兵渡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转移到江北,男兵在南岸死战到底。
王铁环回忆她撤入苏联境内的经过时,讲道:她随着母亲等人在第二路军领导批准下向苏联转移,撤退的队伍由两名抗联战士护送。他们掐准日本人的巡逻时间,迅速从江面上穿过了封锁线,与前来接应的苏军会合。王铁环记得,等他们过了江,护送的两名战友又原路返回。
而就在两名战士过江返回时,王铁环听到了身后的枪声,她和母亲都没说话,眼泪充满了眼眶。事后得知,两名战友返回时牺牲在了和日军的战斗中。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正是七十六年前,不肯退入苏联的抗联将领魏拯民,牺牲在桦甸四道沟密营。
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男儿,从将军到战士,面对最后的抉择,他们护送走了母亲和孩子,却选择了战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保住了孩子,便有了希望。
老兵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历史的脚步让青春最终变成白发。九十岁的王铁环,在我们心中,依然是那个肩负着抗联战士希望的小姑娘。
铁环走了,我宁可相信她是选择了归队。
抗联,我们中国人最痛苦、最骄傲的回忆。
我不禁想,在那个世界里,她会有怎样银铃般的歌声,她会怎样对战友倾诉自己的一生?
我忽然发现,那个时代活下来的抗联少年兵,几乎每人都寿过八旬。
魏拯民只活了三十二岁,赵尚志,只有三十三岁,杨靖宇最长,活了三十四岁,差三天三十五岁。
忽然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倾覆时,杰克对露丝的嘱托:“你一定会脱险的,你要活下去,生很多孩子,看着他们长大,你会安享晚年,安息在温暖的床上,而不是今晚在这里,不是像这样地死去。”
我知道,杰克和露丝是虚构的人物,而少年抗联战士王铁环,不是虚构。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告慰着战友:你们走了,为了我们能活下来,瞧,我是多么珍惜你们给我的这条生命。
当我转身,发现自己泪痕满面。
[责任编辑 张亮]